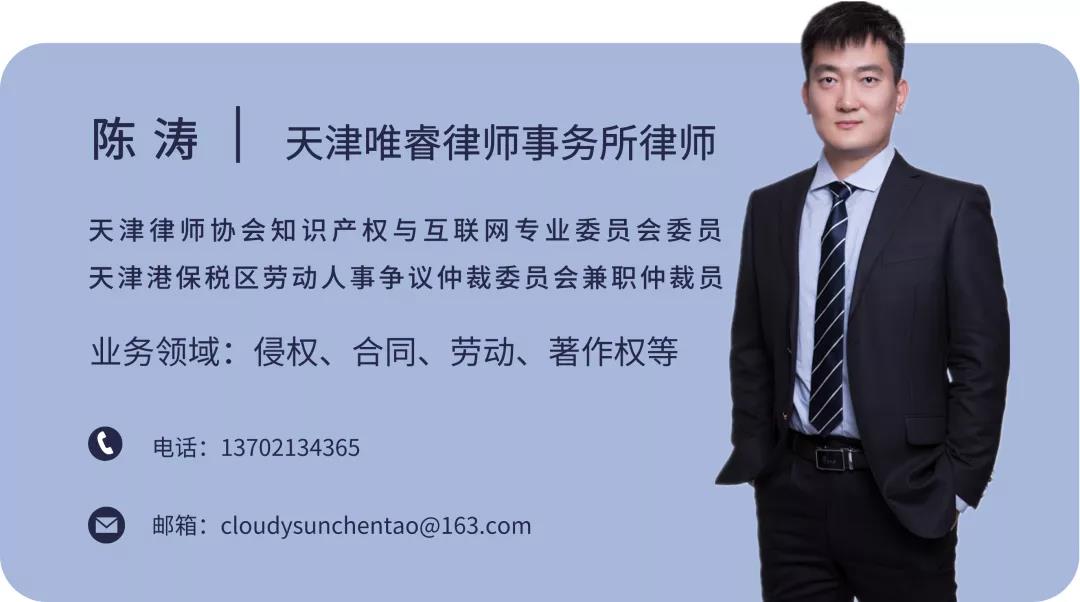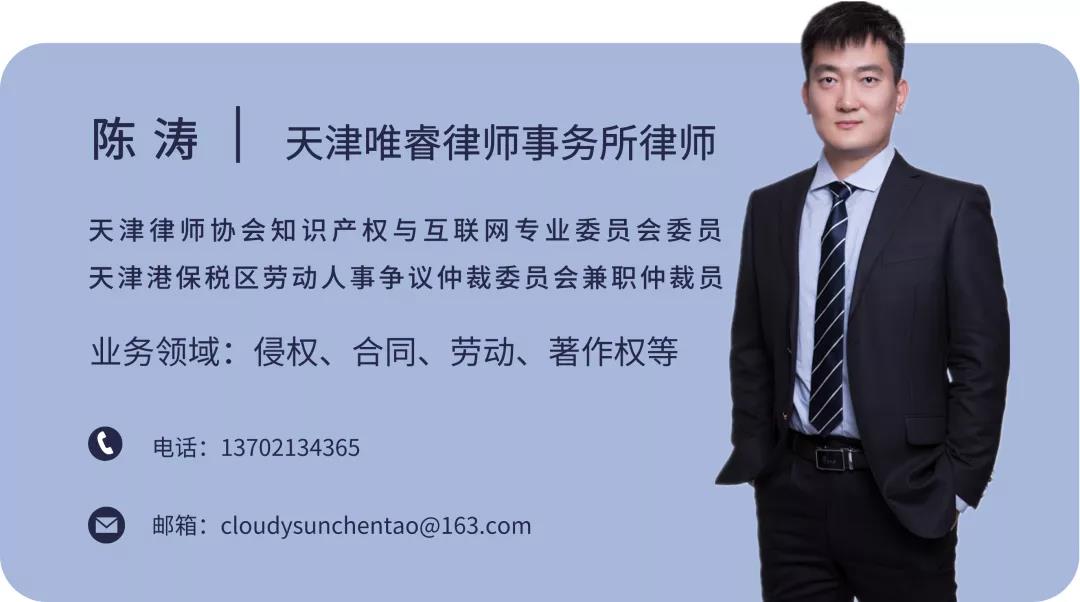摘要:窃电是一种比较严重的违法用电行为,但国家法律法规并未对窃电的含义作出界定,各地方性规范对窃电含义的规定则各有不同,体现出对窃电法律性质的认识也是千差万别。
实际上,窃电是电力法律规范中的特有概念,专指一种违反法律法规的接电用电行为。行为人主观上追求不交或者少交电费的目的,个别情况下,行为人是为了在不具备供用电条件的情况下接电用电。窃电是一个多种责任形式集合的概念,不仅限于刑事责任,还包含有民事责任、行政责任。
关键字:窃电
一、界定窃电法律含义的现实需要
作为电力行业唯一的法律——《电力法》对窃电未给出法律定义,仅在第七十一条中规定了盗窃电能所应承担的法律责任。其后,国务院出台的行政法规《电力供应与使用条例》也只是在第三十一条以列举的方式规定了哪些行为属于窃电行为。《供电营业规则》延续了《电力供应与使用条例》的内容,同时规定了窃电量的计算方法和法律后果。可以说,从国家法律法规的层次上看,都没有对窃电的法律概念作出规范。一些地方规范性文件,有过对窃电法律概念进行定义的尝试。《江西省反窃电办法》将窃电定义为“以非法占用电能为目的,采用隐蔽或者其他手段不计量或者少计量用电的下列行为”;《海南省电力建设与保护条例》则规定窃电是“以非法使用电能为目的……实施的不计或者少计电量、电费的用电行为”;《山西省预防和查处窃电行为办法》认为窃电是“以非法占有电能为目的,采用秘密或者其他不正当手段不计或者少计电量的行为”;《黑龙江省反窃电条例》则认为窃电是“以不交或者少交电费为目的,非法使用电能的行为”,这也是地方规范性文件中较少认为窃电的目的是以不交或者少交电费有关;《天津市供电用电条例》则将窃电行为分为了两种层次,第一种是不构成刑事犯罪的窃电行为,并将其定性为违法用电行为,第二种则是构成刑事犯罪的窃电。供电企业发现上述违法用电行为,应当予以制止,并根据实际情况可以立即中止供电,保护现场,调取和保存证据,依法追缴电费,并报电力管理部门依法查处;其中以非法占有应交电费为目的构成窃电的,移送司法机关依法查处。
从中也能看出,这里的“窃电”目的与黑龙江省的规定是一致的,但该条例中的“窃电”行为的范围与前述国家和地方规范是不一样的,在《天津市供电用电条例》中,“窃电”仅指构成刑事犯罪的情形,不够成犯罪的行为属于违法用电。
这也是实践中,“窃电”的用词较易让人理解为刑事犯罪,而忽视窃电行为中有关民事权益保护的无奈之举。由此也可以看出,在国家层面没有对窃电作出法律含义界定的情况下,各地方对法律意义上的窃电性质的认识上,是有较大区别的。而对于窃电法律性质的不同理解,也会影响到窃电法律责任的不同理解。因此,明晰窃电法律概念的内涵和外延,对于依法追究窃电行为人的法律责任,维护供电企业合法权益,制止窃电行为,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二、界定窃电法律含义的要素
虽然地方法规对窃电法律含义作出了不同的界定,但在规范窃电含义时,通常都是围绕窃电行为本身,即各地方法规都认为窃电是违反法律法规规定的方式接电用电的行为。《电力供应与使用条例》《供电营业规则》虽然没有给出窃电的法律含义,但却明确列出了哪些行为属于窃电行为,其规范逻辑与地方法规是一致的。2.窃电应是一种涵盖有三种法律责任形式的综合概念。窃电并不是刑法概念,与之有关的刑法概念只有盗窃罪。而从《刑法》第二百六十四条规定来看,以窃电方式构成盗窃罪,还需要满足“数额较大”的金额条件,否则也不能构成盗窃罪。但是从电力法律法规对窃电行为的规范来看,窃电的违法性体现为行为人所实施的窃电行为本身,而非实际获得窃电的收益。例如《电力供应与使用条例》第三十一条明确规定为“禁止窃电行为”,并列举了5种具体的窃电行为方式和1种兜底方式,并未再规定行为人实施这些行为是否需要实际造成电能的使用或者未支付电费的后果。显然,电力法所否定的窃电较之《刑法》要宽泛的多。虽然窃电本身也包含“窃”的字眼,但未必属于盗窃罪,其首先应是一种违反电力法律法规的行为。对窃电行为承担法律责任的目的,在于维护安全的用电环境和用电秩序,既是对供电企业经营秩序的保护,也是对社会公众人身财产安全的保障手段。因此,只要行为人实施了电力法律法规所规定的窃电行为,就需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这种法律责任可以是基于供用电合同关系的违约行为,也可以依照《治安处罚法》承担行政责任,亦可以在满足“数额较大”的金额条件时承担刑事责任。从这一角度来看,窃电的法律后果,涵盖了全部三种法律责任形式。盗窃电能的,由电力管理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追缴电费并处应交电费5倍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供电企业对查获的窃电者,应予制止并可当场中止供电。窃电者应按所窃电量补交电费,并承担补交电费三倍的违约使用电费。拒绝承担窃电责任的,供电企业应报请电力管理部门依法处理。窃电数额较大或情节严重的,供电企业应提请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该规定又赋予了供电企业相应的民事权利,可以对窃电行为人采取必要的措施。
实际上,即使没有《供电营业规则》的规定,供电企业也应当天然的享有对窃电行为人采取措施的权利。因为供电企业与窃电行为人同属于民事主体,这种权利属于民事权利,其可以依据供用电合同关系产生,也可以依据财产利益被侵犯的自力救济而天然享有,此时,供电企业与窃电行为人是否具有合同关系就不再重要了。当然,《供电营业规则》以及各个地方性规范文件之所以对供电企业在制止窃电问题上,对供电企业的行为进行规制,源于电力法律体系属于经济法范畴,需要体现一定的国家管理的要求,不能赋予供电企业无限大的权利。当然,不可否认的是,在制止窃电过程中,基于民事、行政、刑事责任三者之间的递进关系以及相关专业性要求,供电企业还是发挥了主要作用的。可见,窃电并非是单一法律责任形式的概念,基于窃电行为,行为人可以承担民事、行政甚至刑事责任,绝非因行为人有窃电行为,只能通过刑事责任追责,而排出供电企业的民事权利。首先,在我国《物权法》框架下,电能不是占有的客体。占有是《物权法》上的概念,其有两个层次的法律意义:一是依据《物权法》第三十九条规定,占有作为所有权权能之一,是所有权项下的一种权利表现形式;二是依据《物权法》第五遍规定,占有是一种独立于所有权之外的单独的物权权利。
无论何种法律意义,占有的客体均应是《物权法》所规定的物。按照杨立新教授的观点,电能属于自然力的一种,而自然力是人工转化得到的二次能源的能量表现形式。而我国《物权法》所规定的物,包括不动产、动产和法律所规定的某种权利,严格讲并不包含电能这种自然力。
虽然杨立新教授认为电能应当属于一种特殊动产,但无论立法、司法解释以及司法判令中,均未能将电能界定为我国《物权法》上的物权客体,也就不可能成为占有的客体。强调窃电行为具有占有电能的主观目的,与现行物权法律制度并不相称。
其次,电能一经使用就会消耗,不具有占有条件。法律上的占有是一种持续性的状态,且能够通过占有的表现形式,向外界展示占有人对某种特定物的权利。由此也可以看出,占有的对象——特定物本身应当持续保持其原物的外在状态。窃电行为人之所以窃电,不在于追求对电能的持续占有,而是使用电能,这种使用就会造成电能的消耗,如果将电能界定为法律上的物,那么电能在使用过程中持续不断的消耗和更新,无法保持这种原物的外在状态。电能从被窃取的那一刻起,就通过电线被输送到用电设备,然后被消耗掉,而这种被消耗掉是一种持续不断的过程,而非某种固定状态的持续。通俗来讲,电能不断的产生、输送并被使用而消耗,我们无法抓取某一特定节点的电能,也无法在某一个特定时刻确定此时的电能究竟是什么状态。显然,法律上的占有客体不应当是一种无法被抓取且无法被清晰感知的东西。即使现实中有通过蓄电池储存电能的方式,但通常而言,蓄电池仅是延缓了电能被消耗的时间,其最终仍会被安装在用电装置上使用,何况电能易被消耗的特点也决定了,即使在蓄电池中的电能,也无法被认定为具有占有可能性的物。因此,窃电所获取的电能并不具有能够被占有的条件。
再次,窃电的直接目的在于使用。一种无法被占有的东西为什么会有人窃呢?这是一种逻辑上很奇怪的疑问。虽然我们不能在法律上找到电能具有物权属性的规范,但是电能作为一种能够被价值衡量的财产,还是可以用法律上有关财产权的规则来理解电能。《物权法》规范物本身的目的在于实现物的财产属性,但其所规定的物的种类和范围,并不能涵盖所有财产,而财产显然应当是大于物的一种概念。凡是可以被价值衡量的东西都可以作为财产,这种财产可以是有形的、无形的、存在于自然界的或者是被人们生产生活创造出来的。电能作为现代社会人们生产生活所必须的能源之一,其本身就具有价值属性,直接体现为电费。当然,电能之所以具有价值,根本原因在于其具有使用价值和商品属性中的稀缺性。因此,窃电的直接目的在于使用电能,驱动用电设施设备,实现生产生活的特定目的,而不是将电能储备起来。窃电的直接目的与正常用电的目的是一致的,都是实现电能的使用价值,两者不同仅在于前者的行为人并不支付或者少支付使用电能的对价,而这也是行为人冒着违法,甚至健康和生命危险实施窃电行为的根本目的。窃电行为人的根本目的是显而易见的,但为何多个地方的规范性文件,仍将窃电目的界定为占有电能?这很可能是受我国《刑法》关于盗窃罪规范的影响。我国《刑法》第二百六十四条将一般意义上的盗窃定义为“盗窃公私财物”,且通常在解释盗窃罪的构成要件时,认为盗窃罪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盗窃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条在规定盗窃数额的认定方法时,用了“盗窃电力、燃气、自来水等财物”的用语,实际上也是将电能作为了盗窃对象,这样一来,“非法占有为目的”,就当然可以理解为“非法占有电能”。由于我国刑法上没有盗窃电能的专门规则,在《刑法》出台之初,盗窃罪所指向的公私财物并不明确包含电能,而盗窃电能作为盗窃案处理的规则是在1997年11月4日颁布的首个盗窃司法解释时方才确立的。因此,在用盗窃罪解释窃电行为时,就会存在一定的逻辑障碍。而如果不将窃电行为的目的界定为“非法占有电能”,似乎就无法将窃电与盗窃罪挂钩,于是,就出现了前述地方性规范文件对窃电目的的错误界定。其实不然,即使行为人通过窃电无法占有电能,但也不影响其构成盗窃罪。盗窃罪的本意是对具有非法占有为目的,所实施的秘密窃取他人财产的行为进行否定性评价。窃电具有盗窃罪的全部特征。其一,行为的秘密性。毋庸置疑,无论是《电力供应与使用条例》还是各地方性规范文件所列举的窃电行为,无一例外都具有违背供电企业意志的私密性,且随着技术的更新,其隐蔽手段更加高明。其二,电能具有经济价值,且能够量化为电费。电能作为具有稀缺性特征的商品,是有一定价值的,该价值就体现为电费。行为人通过窃电行为使用了电能而未付出成本,相应的,供电企业产生了电能的消耗而未能收取该部分消耗的电费,作为电能的经营单位,必然存在经济损失。其三,行为人的主观目的是免费使用窃取的电能,而该部分电能正对应供电企业的损失,于是行为人通过窃电方式侵害了供电企业所应收取的电费,也可以理解为行为人占有了供电企业应得的电费。因此,窃电人通过窃电方式使用电能,其根本目的在于不交或者少交电费,并基于此可能构成刑法上的盗窃罪。窃电行为通常是使用电能和未支付对价的结合,但实践中不乏行为人主要是基于使用电能的窃电,对于未支付电费的违法后果并非其追求的根本,而无法支付电费是由于客观原因所致。例如,成建制的村庄进行整体搬迁之后尚未拆迁完毕之前,某些村民回到原住址居住,由于原址属于拆迁地区,并不具有再新装供电的条件,于是私自引线接电使用。从其主观上来说,村民并不具有不支付电费的恶意,但由于客观上该地区已经无法正常用电,供电企业也不会给这些村民再安装电表计量,即使村民有意交纳电费,也无处计算和交纳。简言之,主观上有用电需求,而客观上不具备装表接电的地区,就有可能出现行为人为了使用电能而窃电的情况。此时,电力法律规范要求其承担窃电法律责任的立法目的在于,行为人的行为客观上危害了供用电安全与秩序。申请新装用电、临时用电、增加用电容量、变更用电和终止用电,应当依照规定的程序办理手续。
《电力供应与使用条例》第二十三条也规定,申请新装用电等均应当到当地供电企业办理手续,《供电营业规则》第十六条则规定:
任何单位或个人需新装用电或增加用电容量、变更用电都必须按本规则规定,事先到供电企业用电营业场所提出申请,办理手续。
未按前款规定办理的,供电企业有权拒绝受理其用电申请
显然,电力法律规范为保障供用电安全与秩序,对供用电关系的建立和履行设置了一定的条件,虽然供电门槛非常低,但对于不满足供电条件的情形,供电企业拒绝供电不仅是法定权利,也是一种义务。相应的,用电人只有在符合国家有关规定的条件下,才依法享有用电权利,不具备供用电条件时,用电人不得违法接电,否则就属于违法行为。
虽然从违法后果来看,其已经符合窃电的构成要件,在满足窃电金额达到量刑条件时,也可能被以盗窃罪论处,但从主观方面来分析,行为人非法占有应交电费的恶意与一般窃电行为人相比要低得多,当然,这种主观恶意仅对其法律后果有影响,对于其违法性的认定并无关联。
三、窃电法律含义的界定
综合以上分析,我们将窃电的法律含义进行重新界定。所谓窃电,是指通常以不交或者少交电费为目的,或者在不满足国家关于供用电条件的情形下,为了使用电能,而实施的法律法规所禁止的方式接电用电的违法行为,窃电行为人基于所实施的窃电违法行为,依法应当承担相应的民事、行政、刑事责任。